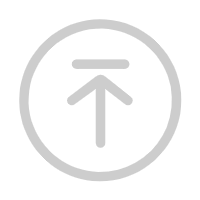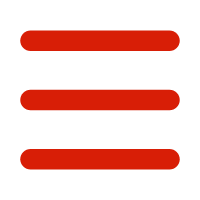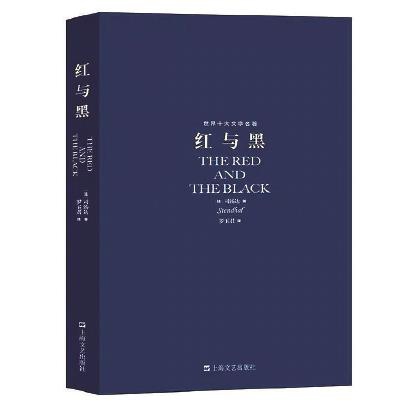
《红与黑》 司汤达 著 罗玉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
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,对十九世纪经典文学的翻译名家一定不会陌生,林纾、傅雷、李健吾、李青崖、闻家驷等等,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,是一种期望用文学启迪民智、用文学陶冶民心,甚至用文字的力量拯救民族的期盼。但在经典作品不断复译、现当代作品持续呈现的今天,更多的、曾经将法国文学大家带入我们视野的翻译家已经渐渐被淡忘,罗玉君也是其中的一位。
提起罗玉君,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她翻译的《红与黑》了。的确,自巴黎大学著名心理学专家乔治·杜马教授向罗玉君推荐了《红与黑》,她与这本书、与法语文学翻译、与文学研究便结下了一生的情缘。从阅读到翻译,从首译到重译,从翻译到出版,这部“撞进了心扉”的作品伴随了她整整三十多个年头,也因此,罗玉君将重译的《红与黑》视作她“生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”。
当然,一次次的复译,迄今的二十多个译本,《红与黑》的汉译已然超越了对个体的意义,而被视作文学翻译的一个典型、一个事件,被关注、被讨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许钧先生组织的关于《红与黑》大讨论,对罗玉君、郝运、郭宏安、许渊冲、罗新璋等五个译本进行过重点比较研究。相较于其它几个译本,罗译本存在着诸如过度阐释偏多、主观随意性偏大,甚至不妥、错译等问题,也不在读者最喜爱的译本之列。但是,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译本,罗译本于1954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一经出版,便广受欢迎,短短几年累计的印刷数量超过100万册。直至1986年郝运译本问世,长达三十年间,罗译本几乎是读者的首选,换句话说,中国读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认识大多是从罗译本开始的。
而另一方面,罗译本中流露出的“主观随意性”,既是个人的,也是历史的。罗玉君在回忆《红与黑》的翻译经过时,表达了对翻译的看法:“翻译是凭借了原作家的符号去寻找原作家的意象,使这意象重现在眼前,灿烂在眼前。”“意象”与“灿烂”二词或许能为她的翻译选择提供某种佐证。《红与黑》中译者有意无意构建起的追求进步、民主的于连的形象,又何尝不是当时经历过战火硝烟、国家初建、百废待兴的中国读者的一种情感需求,以及罗先生所认为的“艺术的社会性”的体现呢。而就罗先生而言,更不能忽视的是她对翻译的热爱、执著,以及排除万难的坚持。翻译《红与黑》,罗玉君前后耗费十多年之久。在战乱的迁徙流离、漂泊不定中,先生“一直把《红与黑》的原文同译稿带在身旁”,这个“患难中养育的孩子”终于在1947年夏天具备了雏形,而后,她又花费一年时间,进行校对和部分的抄写,“每天写得腰酸,每天写得手软,写得朵朵黑云,从我眼前飞来飞去”,才将这个难产的孩子最终“哺育成人”,而翻译也如是成了罗玉君人生中最亲密的朋友。
如果说《红与黑》的汉译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机缘,那么翻译乔治·桑则是气质契合的选择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罗玉君先后翻译出版了乔治·桑的六部长篇小说,包括已有前译的《魔沼》《弃儿弗朗沙》,首译的《小法岱特》,两部童话故事《祖母的故事》和《说话的橡树》以及社会小说《安吉堡的磨工》。她还撰文《乔治·桑和她的作品》,介绍其人其作。一系列中译本的问世以及相关介绍文字的发表,掀起了乔治·桑在中国译介的小高潮。

乔治·桑
改革开放之后,罗玉君重拾翻译乔治·桑的热情,又出版了《比克多尔堡》和《印典娜》两部译作,而当时,先生已因身体原因退休多年,她顽强地与疾病抗争,争取一切可能多译介作品。她曾有意翻译30部左右乔治·桑的作品,形成《乔治·桑全集》,并打算撰写《乔治·桑传》,尽管这些愿望最终未能实现,但罗玉君常年醉心于乔治·桑作品的翻译,她对这位法国女作家的喜爱体现在每一部译作的字里行间,充盈着悠长的译介旅途。这种喜爱,既有基于性别的,也有基于经历的,但更重要的是基于观念的——她们惺惺相惜,通过作品、文字的“神交”,跨越了语言本身的障碍,达到了气质与精神的契合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在语言风格上,乔治·桑以其细腻的笔触、朴素简洁的用词、自然流畅的行文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中独树一帜,这一点与罗玉君本身自然流畅的行文风格颇为贴合。在既忠于原作,又兼顾民族的欣赏和表达习惯的翻译主张之下,罗译的乔治·桑版本不仅广受读者的青睐,也被收入到学校的课本中。
早年的翻译家,常常有两类,作家型的和学者型的,罗玉君应该更偏向后者。1933年,她以优异的成绩荣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。之后不久,便决定与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丈夫李珩一起归来,报效国家。她先后任教于多所高校,也曾是文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。1951年,罗玉君选择随丈夫回到上海,并应聘成为才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专门教授外国文学。她辗转多个城市、多所学校,重又回到文学梦、翻译梦萌芽的地方,她的母校,而这所兼容并蓄的学府,它的“前世今生”已然拥抱和滋养了周煦良、孙大雨、叶治等一批知名的翻译家,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另类的心心相印呢。
进入华师大之后,罗玉君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在教书上。她操着一口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,引领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,热心指导他们的写作和翻译。同时,她继续潜心译书、研究文学,她的译作与评论总是相伴而生,她的文字既不失女性翻译家的敏锐与细腻,又不乏学者的冷静与理性。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性翻译家、学者,罗玉君以刻苦的态度、出众的能力打破了时代的规约和性别的藩篱。
“教书、译书,这是我的两大事业,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。”罗玉君这样说过。曾经,她的足迹留在了国内外的多所高等学府,她的翻译文字走进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里,而今,斯人已逝,文字之外,留给我们后辈的,是对翻译这项事业的坚守,对自身所热爱之事物的追求。或许,这种精神力量比文字本身更为珍贵。
来源:文汇报
作者:沈珂
编辑:周敏娴
责任编辑:宣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