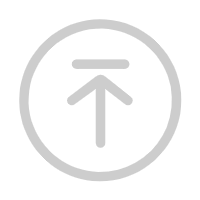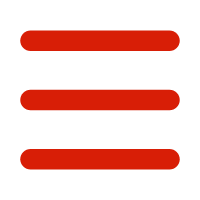日前,ag平台 2021级德语系周子仪同学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了书评——《黑塞与托马斯·曼: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友谊》。德语系黄雪媛老师推荐本文:“文风稳健,醇厚,隽永,后生可畏”。”而《赫尔曼·黑塞与托马斯·曼书信集》也入选了本年度译文双年选决选作品,毛尖教授评价称:“两位大佬的灵魂絮语,译笔既忠实传达家长里短的书信风格,也体现了两位世纪型男的精神等量。”
让我们跟随周子仪同学的笔触,领略这段伟大传奇的友谊。
交响乐与民谣的碰撞、融合
托马斯·曼出生于富庶的汉萨同盟世家,自幼浸润于吕贝克贵族“精英文化”的氛围。父亲留下的丰厚遗产为曼的创作提供了经济保障。曼旨在通过创作树立个人风格,以反讽的笔法与寻常作家拉开距离。他视自己为瓦格纳、歌德、席勒等德国古典文化巨擎的正统继承人。其作品《魔山》是现代欧洲精神思想的镜像世界,《浮士德博士》是一部以文学描绘音乐的鸿篇巨制,《沉重的时刻》《绿蒂在魏玛》是曼为席勒、歌德两位文化名人所勾勒的肖像。1903年,黑塞在为曼的小说集《特里斯坦》所写的书评中公开称赞曼有成为“全能艺术家”的雄心,是一个能从容自信地担起宏大题材的大力士,也能将细节刻画入微,自得地游走于宏大与精妙的“魔术师”。

托马斯·曼(1875-1955),德国著名小说家,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1901年长篇小说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问世,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,1924年因长篇小说《魔山》闻名世界。
与曼的野心勃勃不同,黑塞笔下的字里行间萦绕着浓郁的自然气息,作品中反复出现去工业化、回归自然、追求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主题。黑塞成长于一个清贫的施瓦本新教家庭,成人后,他与父母的虔诚主义道德观和严谨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。黑塞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远离政治中心,质疑现代文明,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“边缘人”,显然,这样的人物即是他自己生活经历的写照。但是,“去政治化”并非冷眼旁观、不问世事,黑塞心忧世界,关怀人性,深入探索如何在个人身上克服时代的弊病。“荒原狼”哈利·哈勒游历了可怖的内心地狱,在撕碎了虚无与混沌后重建真实的自我;辛克莱在少年德米安的指引下走上了寻找“自我”的曲折小径,他笔下的人物,都有一种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果决,这正与他的名言相契合:“为使可能之事出现,必须反复尝试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赫尔曼·黑塞(1877-1962),20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,被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,其代表作《荒原狼》(1927)曾轰动欧美,被托马斯•曼誉为“德国的《尤利西斯》”。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看似曼与黑塞选取的题材、文风、写作偏好迥然不同,两人生活经历的重合却使得两人在关于某些重大问题,如道德与精神、艺术与真理、文学与政治的看法相一致。在两人的书信集中,读者能够清晰地感知一种殊途同归的写作观。
黑塞在一战期间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,呼唤和平与理性,试图以人道主义代替殖民主义与沙文主义。“爱比恨更重要,理解比愤怒更重要,和平比战争更重要”,黑塞在他的反战散文《啊,朋友,不要这股腔调》这样写道。文章一经发表,黑塞遭到民族主义者的诬陷与谩骂,此番攻击让他的事业与心理陷入双重危机。1923年,黑塞加入瑞士籍,以远离笼罩德国的近乎非理智的狂热思想。黑塞曾于1926年加入普鲁士艺术学院,但四年后退出,理由是他极其不信任诞生于真空和战后的筋疲力尽的魏玛共和国,“无疑将会经历一场腥风血雨”。如今回看,黑塞对社会现状的见解可谓洞若观火。然而,众星拱月的文化名流托马斯·曼对当时的政治路线仍有信心,甚至还在1931年写信给黑塞劝说他重新加入学院,理由是“学院在民族主义思潮前不会有任何妥协顺从”。短短两年后,纳粹当政,要求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成员向当局宣誓效忠。托马斯·曼毅然辞去学院职务,离开德国以躲避纳粹的迫害,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流亡。
相似的遭遇让黑塞与曼先后意识到,必须同那些心爱的、长期用自身鲜血滋养的理念告别,“德国大师”与“荒原狼”自此走到了一起。20世纪30年代起,他们开始广泛通信。相隔万里,见字如面,近百十封书信见证了两位文豪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。
日常琐碎与伟大传奇的巧妙平衡
书信集的扉页印着黑塞与曼两人年轻时的肖像照。两个青年面容俊朗,但表情严肃,眉头微微蹙起,眼神忧郁深邃,俨然一副沉思状。不过如果继续往下读,翻到1932年摄于圣莫里茨的两人在雪地里的合照,读者会惊喜地发现,不苟言笑的两人在见到挚友后,放松了紧绷的神经,露出喜悦之情。1934年,黑塞与曼在巴登相聚,曼用三个下午的时间为黑塞朗读了他刚写成的杂文《与堂吉诃德航海的节选》。摄于1934年的合影中,身形瘦高的黑塞头戴礼帽,身着风衣,单手插兜,微微抬头,向曼致意;画面右侧的曼氏同样一身正装,双手背在身后,嘴角上扬。翻看两人其他的照片,可以推测,这些可能是两人为数不多的,在镜头前展现笑容的场合。

黑塞(左)与托马斯·曼,1934。
无论是胶卷世界还是纸张世界,黑塞与曼展现给彼此的都是有笑有泪、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。黑塞的头痛病和时不时发作的眼病与肠胃病,抱怨夏季纷至沓来的访客让他与妻子的生活变得热闹过头,瑞士冬季的阴冷天气耽误了他的工作效率。他也会给曼寄去他手绘的明信片,絮絮叨叨诉说自己与妻子为自家花园的园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,“我在花园里劳动了好几个钟头,身上脏兮兮的,臭得像烧炭工一样”。黑塞写下的诗歌和散文也都漂洋过海,出现在了曼的信箱里。
曼是黑塞忠实的朋友与听众,他热情地赞美黑塞的诗集:“旋律的宝藏!纯净的艺术!”也许是为了宽慰老友,曼也在书信里大吐苦水,称自己饱受坐骨神经痛的折磨,周旋于难缠的出版商与不实的舆论。他辛辣的幽默似乎只有黑塞能消化:“您(黑塞)看起来像个睿智又孤僻的老花匠,而妮侬女士(黑塞的妻子)显得活泼又聪明。”一封封书信拼凑出一个个日常的镜头,读者由此能一窥两位大文豪的生活细节。
除此之外,黑塞与曼也会探讨彼此作品的高超与不足,动荡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与德国思想界的新旧之辩。曼折服于黑塞的《荒原狼》,并在自己的小说《约瑟的青年时代》中化用了少女驯化荒原狼的故事,以表达对黑塞的敬意。曼追求宏大世界观的勃勃野心也感染了黑塞,《玻璃球游戏》的宏大精妙或许归功于曼对黑塞的启发。伍尔夫对巨作的诞生有这样的论断: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、独立存在的;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。那些散落在书信里的真知灼见与奇思妙想,是黑塞与曼作品的最好脚注。
身处异国他乡的两人反复思考着国族的意义。二战期间,两人对于“德国气质”都有了重新的考量。黑塞在遥远的东方开拓自己的精神版图,古老的东方智慧成为支撑他继续写作、生活的精神养料。他梦想在不断堕落、腐朽的旧世界毁灭后,创造一个年轻、美丽又清白的极乐世界。托马斯·曼坚守自己“市民阶级的艺术家”的身份,创造的主题仍然以圣经故事、中古传说为蓝本,但他坚决反对文学的政治化。“在这种说谎成性、集体狂欢、自我麻醉和秘密犯罪的气氛中,我会死的。”在晚年所写的长篇小说《浮士德博士》中,曼用与魔鬼做交易的音乐家形象暗喻德国的命运,出卖灵魂以获得世界大权。保持文学创作免于政治干扰,坚持接近尘世正义,探索美与真理的奥义,是曼的人生原则。
在这部书信集里,鸡毛蒜皮的“轻”中和了哲思沉吟的“重”。在这种张弛有度的阅读节奏中,书页间仿佛流淌出一曲交响乐章,既有涓涓细流的和缓,也有骇浪惊涛的澎湃。

托马斯·曼(左)与黑塞,1932。
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友谊
曼与黑塞的友谊始终保持着一种诚敬的距离,一种极具分寸感的亲切。他们彼此以“您”相称了一辈子,有一回曼在给黑塞的信中试图改称为更为亲昵的“你”,被黑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。歌德与席勒历经坎坷、完成思想上的“双向嬗变”后才成为彼此可靠的战友;卡夫卡与布罗德促膝长谈,掏心掏肺。黑塞与曼的友情讲究平衡与克制,就像他们推崇的人生平衡术一样。曼在1935年写道,“我是一个平衡者,船有向右翻的危险时,我会本能地向左靠,反之亦然。”
平静的水面潜藏着汹涌的波涛,冰山主体的巨大坚实往往不为人知。曼与黑塞的友情看似克制,但在对方遇到恶毒攻击时,这对“灵魂知己”也会毫不犹豫为好友辩白;他们心系彼此的家人朋友,总会在信里问候他们的近况或致以问候。曼折服于黑塞的才华,认为其作品“纯洁、大胆、梦幻、睿智,充满传承、连接、记忆和隐秘”,早在1933年以前,他就力荐黑塞获诺贝尔奖。不爱交际、独来独往的黑塞即使不出席曼的寿宴,也会特地为他写贺词,感激他的毕生巨著和他始终坚持的创作理念,希望这种理念能构成一种新的“世界道德”。战争时期,两人都被祖国抛弃,被同胞攻击,昔日的溢美之词化作淬了恶意毒液的利箭射向他们,支撑他们走完这条艰难道路的,或许要归功于友人间的相互扶持与对未来的乐观向往。曼给黑塞75岁生日贺信的结束语是:“再见,蹚过给予我们梦想、游戏和文字慰藉的泪谷的亲爱老友。”黑塞的回信同样诚恳:“老友,若您先于我‘长颂尘世’,我会伤心沉默。”

托马斯·曼、卡佳·曼、妮侬·黑塞、赫尔曼·黑塞(从左至右),1932。
1955年夏,曼因血栓在瑞士去世,黑塞得知噩耗后,久久不能从失去亲爱老友的阴霾里走出来。在刊登于《新苏黎世报》上的告别信里,黑塞预言曼的作品将会被世人无限怀念,德国的读者将会真正理解他的作品。事实确如黑塞所言。两人的作品都被后世反复研读,他们隽永的友谊同样为人称道。
作者:周子仪 华东师大2021级德语系本科生
推荐人:黄雪媛 华东师大德语系教师
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